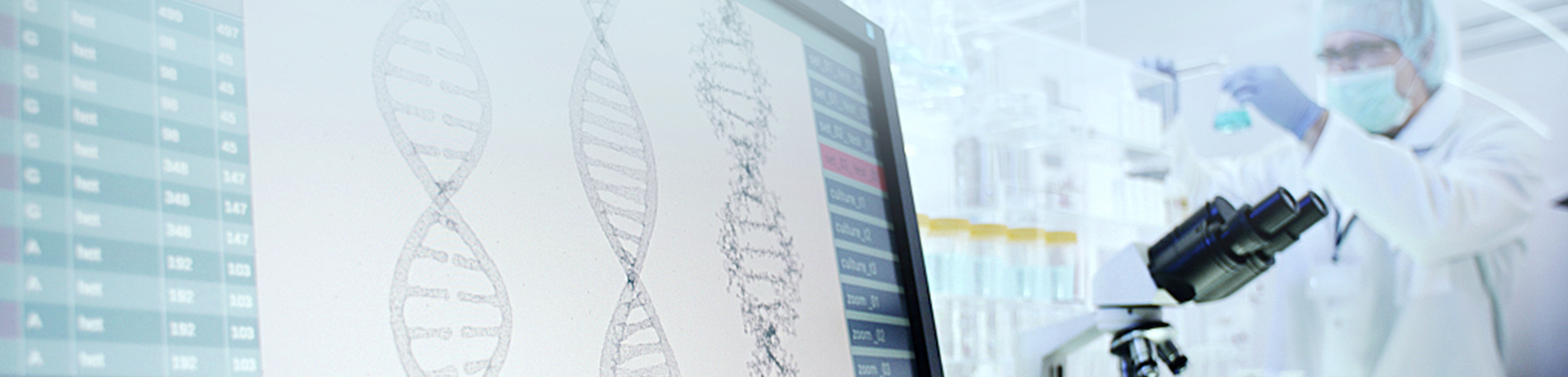
近日,國家醫保局辦公室印發的《關于進一步做好醫療服務價格管理工作的通知》(下稱“通知”)全文公布。通知指出,近年來存在宏觀管理相對薄弱、價格杠桿功能發揮不充分、項目管理引導作用不突出等問題。通知罕見地對高值醫用耗材隱藏在醫療服務中的定價,以及新增醫療服務價格項目出臺可操作性很強的監管指引。通知將對醫藥產業特別是與醫療服務聯系緊密的高值醫用耗材,帶來深遠影響。
醫院面臨“雙總控”:新增價格總量調控
2021年,為貫徹落實中央深改委第十九次會議精神,經國務院同意,國家醫保局等八部門聯合印發《深化醫療服務價格改革試點方案》,標志著新一輪醫療服務價格大規模調整的進程啟動。按照國家醫保局統一部署,河北省唐山市、江蘇省蘇州市、 福建省廈門市、 江西省贛州市、四川省樂山市被確定為首批試點城市。7月1日,國家醫保局在廈門舉辦深化醫療服務價格改革試點工作推進會。與其他領域醫保改革試點以1~3年為周期不同,醫療服務價格改革相當審慎,不僅只選擇5個地級市,還以5年為試點周期,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嚴防醫療服務價格“普漲”引發民意反彈。
通知顯示,價格管理總量調控的思維已經從5個試點城市拓展到全國所有醫保統籌區。今后,公立醫院將進入“雙控”階段,運營管理將面臨緊約束。一方面,繼續對分配到每家醫院的醫保資金進行總額管理。當然,實施醫保按疾病診斷相關付費(CHS-DRG)、按病種分值付費(DIP)地區,可能淡化醫院層面的總額管理,逐步過渡到更宏觀的區域層面總額管理,以及更精細化的按不同顆粒度的疾病(如:單病種、疾病組、組合病例)打包付費。
另一方面,通知發布后,全國每家醫院的醫務性收入對應的醫療服務價格都要接受總額調控。之前,公立醫院想在國家醫改降低藥品耗材收入之后直接實現醫療服務價格“普漲”,如今,這一“躺贏”的念想將被打消。
國家醫保局的政策導向相當明確:一個是要防止“左手倒右手”,將集采擠出的藥品、耗材虛高價格的水分,全部平移到醫療服務價格上,繼續造成群眾看病負擔;相反,要讓集采降下來的藥品、耗材價格的改革紅利中的相當部分返還給參保群眾。再一個是調價要“有升有降”,價格調整總量如何做大,除了降低藥品、耗材費用實現“騰籠換鳥”,也包括下調部分偏高的醫療服務價格。比如規定:對于社會捐贈、應使用政府性資金購買的大型檢查治療設備,既然成本比市場化購入低,對應的大型設備檢查治療項目等領域醫療服務價格也要適當調低,這也將降低醫院實施過度檢查、“以檢補醫”的動力。
那么,今后醫療服務如何設置總額調控?廈門試點可以作為一個參考,該市公立醫療機構以歷史收入水平(不含藥品、衛生材料收入)為基數,綜合考慮經濟發展水平、醫藥費用規模和結構、醫保基金籌資運行、公立醫療機構運行成本和管理績效、患者跨區域流動、新業態發展等因素,確定每年的調整系數。歷史基數乘以調整系數后,就得出全市范圍內可用于調整的醫療服務價格的總金額。
“一升一降”的邏輯:重視技術勞務價值
對于作為公立醫院高質量發展試點的大型高水平醫院,技術服務性收入占醫療收入的比例,到“十四五”期末力爭達到40%左右,“十五五”期末力爭達到60%左右。
為實現“降醫藥產品,升醫療服務”的上述目標,價格管理是一項重要政策工具。對醫生而言,能夠從臨床診療服務獲得合理回報,且合理回報的提升標準不是藥械銷售術而是過硬醫術,更有利于其形成“不愿腐”的動力;放大到整個醫院,長周期、高投入的專科能力建設獲得合理的價格激勵,有利于引導醫院從過度追求“以藥補醫”“以耗補醫”“以檢補醫”回歸提升診療能力的本業。
通知體現的正是重視技術勞務價值,使價格與價值趨同,讓部分偏低的醫療服務項目“大大方方地漲價”。哪些醫療服務項目有上調空間呢?通知提出兩個60%的標準:從單一項目看,治療類、手術類、中醫類中遴選價格長期未調整、技術勞務價值為主(價格構成中技術勞務部分占比60%以上)的項目;從單一輪次看,每次價格調整方案中技術勞務價值為主的項目數量和金額原則上占總量的60%以上。還有,為告別公家單位“吃大鍋飯”,文件規定,對技術難度大、風險程度高、確有必要開展的醫療服務項目,從而基于醫療質量和技術水平拉開服務機構的差異。
公立醫院決不能產生“調價依賴癥”,將醫療機構自身管理內部責任,比如臨床能力、財務管理、內部薪酬分配,全都寄托于醫療服務價格調整帶來的增量收入空間,企圖通過一次性調價解決醫院高質量發展的一切問題。這既不符合精準化的醫療規律、精細化的管理學規律,也很可能突破醫療服務價格總額調控的“天花板”。歸根到底,公立醫院要克服“賺快錢”“搞政績工程”的路徑依賴,醫院管理層要勇于自我革命,優化臨床管理權治理,克服利益分配不公,并舍得投入學科建設,沉下心來推進中長期財務改革和內部薪酬改革。
各類高值藥、高值耗材企業、醫療人工智能企業則要克服“以產品取代醫療”的路徑依賴。今后,凡是有利于公立醫院提質降本增效的項目,企業就要大張旗鼓去做,用產品價值本身打動醫院進入臨床放量;凡是為醫院開拓新的創收渠道但以犧牲患者權益為代價的項目,或者“以耗代醫”讓基層醫生、低年資醫生退化為只會開藥、放設備、點回車鍵“懶漢”的項目,企業切記勿做。
須知,今年,在國務院醫改領導小組的統一部署下,全國醫改工作會議首次提出協同推進醫療服務價格、醫保支付(國家醫保局主管)、人事薪酬(國家人社部主管)、績效考核(國家衛健委主管)等改革。如果公立醫院發起狠來提升弱勢專科、弱勢團隊的技術勞務價值,無法提供總體解決方案的企業就會被醫院領導、科室主任拒之門外了。
監管博弈:遏制“醫耗不分”與過度醫療
如果說,長期實施的醫保總額管理只能管到醫保支付范圍內的資金去向和使用績效;那么,價格總額調控可以管到非醫保支付的所有醫務性收入,既包括隱藏在醫療服務項目中的高值醫用耗材,又包括醫療服務中的虛增項目、虛高價格。
對耗材廠商而言,隨著公立醫院對藥品、耗材占醫院收入的比重(俗稱“藥占比”“耗占比”)逐步壓縮,高值醫用耗材相對于藥品具有中間品的特性,一些耗材隱藏在醫療服務價格中立項收費,從而維持其價格的虛高水分,進而在醫院獲得醫務性收入后再和醫院分賬。如果這些耗材恰恰不在醫保報銷范圍內,且不受醫保總額管理的限制,就會將高價格轉嫁給患者,從而加重其自費負擔。
通知著力在“醫”和“耗”之間劃清邊界,遏制一切“鉆制度空子”行為:首先,對以新設備新耗材成本為主、價格預期較高的項目,要“醫耗分離”開展創新性、經濟性評價;其次,對合并在醫療服務價格項目中、不單獨收費的耗材,要求在集中帶量采購降低物耗成本之后,適當降低醫療服務項目價格,嚴防虛高水分“由耗到醫”;再次,在每一輪的價格調整方案中,以技術勞務價值為主的項目數量、金額原則上要占總量60%以上,要嚴防“以耗綁醫”,公立醫院濫設以設備物耗虛高價格為主的項目。
對公立醫院而言,即便在“以耗補醫”利益通路被封死后,醫療服務的“調價”絕不能異化為虛增項目、哄抬價格,大搞多看病多賺錢的新型過度醫療行為。通知規定,避免按特定設備、耗材、發明人、技術流派等要素設立具有排他性的醫療服務價格項目。這意味著,以往通過挖角某位“名醫大師”、吹捧某項“獨門秘術”、花些錢采購某款進口手術機器人,公立醫院就能走上為高端服務“量身定價”的創富之路,如今不再成為可能。長遠而言,地方政府主官、公立醫院管理層還是要在醫院內外部治理方面下功夫,要根除公立醫院過度逐利的動機,真正意義上回歸公益性,至少要將其利益實現機制與患者的健康權益保持一致。
(來源:中國醫療保險)